世界在书店中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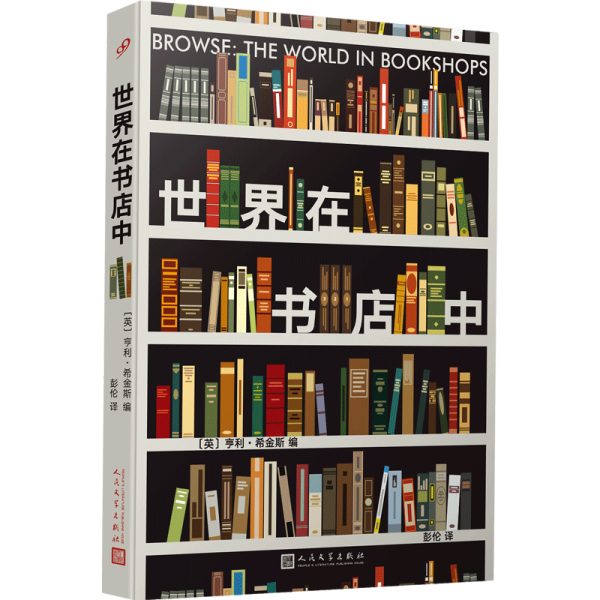 |
内容简介
☆十三位作家写给书店的“温暖情书”!
☆从这里开始,让你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爱书人!
这本书不是地名索引,不是世界书店指南,
而是十三位作家对书店这种特殊空间的私人回忆。
对他们而言,书店是一种药或一帖处方,是一座秘密花园,
是抗议世界其他地方泛滥的陈词滥调、巧言令色的舞 台,
也是一个安全、理智的所在,
是一个既是灯塔也是洞穴的地方。
名人评论
◆书店永远都在产生新的渴望,永远都在我们心中播种渴望。这种渴望会休眠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突然破土发芽。这就是它们的魔力:灵感在我们心中激荡,偶遇唤醒陌生的热望,梦想越来越大,顿悟照亮了心灵。——亨利•希金斯
◆四十年中一直跟我彬彬有礼地点头示意、但仅限于说“你好”“谢谢”“再见”之类客套话的利基先生,从他的书店,从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书店,现在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书店,给我回了这封邮件。“几十年的时间在我们周围堆叠起来,”他写道,“这本品相很好。它得归到那种如果你有幸碰到、你会读一遍、但不会再读的书里去,这类书令人沮丧,数量众多。”祝愿我们在书店里都有这样的幸运。
——阿莉•史密斯
◆我爱二手书店。我爱旧书,爱它们的霉味,爱卖旧书的人们。我爱寻找我从没打算找到的东西。
——安德烈•克考夫
◆“这里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我们经过福伊尔书店旧址时,我说,尽管我也不确定究竟什么是在那里开始的——也许根本不是开始。也许它就是终点。
——伊恩•桑瑟姆
◆一家好书店是这样一个地方: 你为了找一本书进去, 出来时却买了你原本不知道存在的书。 文学的对话就这样得以拓宽, 我们体验的疆界就这样在反抗局限中向外推进。
——胡安• 加夫列尔• 巴斯克斯
◆在这个多变的城市里, 我能找回这样一个空间, 让我感觉它是不变的“家”。
◆绿棕榈书店已不复存在,但它的书,它的言辞,它的经验, 仍在这个世间, 在我的心中。
——斯特凡诺• 本尼
◆“爱书人驻足”书店是一个变化世界中固定不变的点, 哪怕它内部几经变动。
——伊恩• 辛克莱
◆伊斯坦布尔的书店和它们的杂乱与多元,一直与我同在。我到哪里都带着它们,就在我的头脑中,在我的灵魂里……
——艾丽芙•沙法克
作者简介
亨利•希金斯(Henry Hitchings),生于197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历史评论家和语言学家。2005年,以《约翰逊博士的词典》一书获得英国现代语言学会的独立学者最佳作品奖。2008年,以《英语的秘密家谱》一书获得约翰•卢埃林•里斯奖和萨默塞特•毛姆奖。此外,还著有《如何读懂经典》《谁害怕简•奥斯汀》和《语言战争》等作品。
原文摘录
如果你从未去过切尔诺夫策——我基本上百分之百确定你没去过——我只能告诉你,一百年前这座城市的书店里曾经卖过德语、罗马尼亚语和意第绪语的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里的市民大多数都说德语——毕竟,它那时属于奥匈帝国。然后,罗马尼亚王国替代了奥匈帝国,罗马尼亚语也替代德语成为这座城市的书面语和口语。自那之后沧桑巨变。如今唯一的问题是这座城市的历史主要是由诗人记录的。切尔诺夫策永远都有太多的诗人;散文体作家则永远稀缺。即使到今天,在被欧洲政治史以它惯常的无耻粗鲁将这座城市和市民从苏联“驱赶”到一个独立的、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情况依然如此。 我清楚地记得进人新秩序的这段过渡时期:一九九一年,杂货店的货架空空如也,店员态度傲慢恶劣;而书店里,店员们茫然地站在放满苏联文学作品的书架前,这些书再也没有人会看——杂货店和书店的反差是何其鲜明。书店是危机的第一批牺牲品。它们乖乖地关门,没有抗议,甚至没有试图为了生存而挣扎。在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后的最初几年,基辅的一百家书店仅剩下十家。我尤其痛心的是诗歌书店的倒闭——这座城市唯一只卖诗集的书店。在苏联时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我在那里发现了一本立陶宛诗人马塞利乌斯·马丁奈蒂斯的诗集《库库提斯之歌》。我翻了翻,读了其中几首诗,马上买了,花了我七十九戈比。也许我把数字记混了……这个七十九可能是指那年是一九七九年?记忆是靠不住的,选择性记忆是另一码事。我依然能背诵那本诗集里的许多诗,逐字逐句。我能背诵是因为当时我给那些最喜欢的诗配乐,把它们变成歌曲,在钢琴上自弹自唱,我起码把他的二十首诗编成了歌。即使现在我还会唱其中一两首。我太喜欢马丁奈蒂斯的诗了,马上认定他早已去世。对我来说似乎总是如此:我发现了一些喜欢的好诗,然后对作者做一番研究,结果发现他已经死了。总是这样。这导致我得出结论:好诗不可能是在世的诗...
书评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吴玫(来自豆瓣) 来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4343480/
40岁那年,丹麦作家多尔特·诺尔斯的短篇小说集《空手劈》上市,集子里的故事受到好评后,作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多尔特·诺尔斯在严寒中经过哥本哈根的老国王路,十字路口远端的一家书店看上去小而温馨,她便穿过马路跨进了温暖。
店里只有一名已不年轻的女店员,多尔特·诺尔斯打过招呼后便去浏览书架上的书。她看到了自己的《空手劈》,但被塞进了书架里只露出了个书脊。多尔特·诺尔斯多么希望某个陌生的顾客会看到她的《空手劈》并翻开读起来,还越读越喜欢。于是,她把这本书放回去时没有塞进书架而是让它面朝外靠在书架上。“我忍不住把它的封面朝外摆放了”,告别时,多尔特·诺尔斯笑着告诉女店员,没想到因此激怒了她。女店员从柜台后走出来,从多尔特·诺尔斯的身边挤到书架那里,踮起脚尖把《空手劈》插回原处后生气道:“你们都想让自己的书被读者看见,拿出来摸,可你们乱放书,我找不到,就没有办法卖你们的书了!”说着,还把多尔特·诺尔斯撵出了书店。 回到家里,气极而泣的多尔特·诺尔斯给女店员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管理书店的人知道,他也应该尽量在顾客身上看到某些他们不见得自知的更重要的品质。他也明白,他就像是文学延伸的手臂……”就是这句话,让多尔特·诺尔斯这篇《亲密》成了《世界在书店中》所有文章中,我最喜欢的一篇,因为,它戳中了当下我们与网上书店关系中的尴尬。我们去书店并愿意久久地盘桓其中,除了想在列队欢迎我们的书籍中寻觅到中意的那一本外,也期待能邂逅一名如书籍延伸的手臂那样的店员。如今,这种期待已被网上书店吞噬得差不多了,买书者与卖书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几乎荡然无存。
于是,愈加怀念城市喜欢把书店当做自己独特风景的往日时光,愈加怀念人们喜欢将约会安排在书店里的往日时光。怀念不如相见,可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集体走向式微的当下,我们恐怕只有通过作家们记忆中的书店来遇见全盛时期的书店的无限风光了。
“莱内尔书店里一直都放着好几把皮质扶手椅,让人感觉好像是在谁家的客厅,而我们读者坐着,就感觉像是在一个好客的人家里参加大派对。这种感觉在今天许多书店里是找不到的,在这些书店里,读者好像被视为入侵者,进来浪费时间,可能什么都不买,而店员对浏览书籍这种神圣的习惯不以为然,也许因为他们从没这么做过。而坐在那些扶手椅中,我会计算自己作为学生的零花钱,在钱包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对自己想要的书,完成几个小时的神游”,选自哥伦比亚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一篇题为《两家书店的故事》的这段描述,显而易见是在比较两家书店给予他的大相径庭的感受。
那么,描述中所指的两家书店对应的就是文章标题中的两家书店吗?不。在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看来,店员对浏览书籍这种神圣的习惯不以为然的书店,根本配不上书店这一称号。那么,除了莱内尔书店外,《两家书店的故事》中的另一家,是哪一家?那是一家名叫“中央”的书店,那家书店的老板对作家年少时对他格外温情,那段情谊烙印在了作家的记忆深处。
由英国作家亨利·希金斯编、彭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在书店中》,汇编了13位作家对书店这种特殊空间的私人回忆。惟其如此,13篇文章的每一篇,都倾注了作者对自己难忘的书店的复杂情感。而意大利作家斯特凡诺·本尼留在那篇《绿棕榈书店》中依依不舍的深情,特别令人怦然心动。
罗伯特·罗韦尔西是个诗人,他那家开在老旧地下室的绿棕榈书店,是博洛尼亚作家和学生经常聚会的地方,可见,罗韦尔西是个包容性很强的书店老板。但熟悉罗韦尔西的人更知道,他其实是个毫不妥协的人,因此,罗韦尔西得了个外号,善良的魔鬼。再怎么善良,魔鬼终究是魔鬼,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将“魔鬼”这一令人恐慌的词按在善良的罗韦尔西的头上?斯特凡诺·本尼在文章中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天,一位衣着考究的绅士走进书店,在书架间逡巡,不情不愿地随手翻阅,然后指着一本很贵的艺术树说,“我要那本书。送人,我想给人一个好印象。”“很抱歉,”罗韦尔西带着讽刺的微笑答道,“那本书已经卖给了东京的二本木教授。”不得已,这个顾客又要买其他书,但每本他想要的书,据罗韦尔西称都卖给了某个神秘人物。最后,这个顾客怒气冲冲地空手而归。 不用说,衣着考究的绅士所选的每一本书,都是绿棕榈书店的在售商品,罗韦尔西层层设卡阻断衣着考究的绅士如愿,是因为他书店的数条经营理念中有一条居然是“书是挑顾客的”,如此看来,罗韦尔西岂止是书籍的手臂延伸,他就是那些书籍的媒人,要确保将它们送入真心呵护它们的读书人的怀抱。对开店就是为了挣钱的老板而言,绿棕榈书店的经营理念有些匪夷所思,市场没有因为罗韦尔西爱书如斯而不惩罚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文化的奇迹绿棕榈书店,于2012年随罗韦尔西的去世而倒闭,去世前,他已经非常贫困。
《绿棕榈书店》的读者一定会同斯特凡诺·本尼一样,将崇敬之情献给已在天堂的罗伯特·罗韦尔西的吧?他经营绿棕榈书店的那段时光里,始终在创作一首赞美诗,赞美人与书店之间两情相悦的美好情感。
《世界在书店中》所收文章的13位作者中,有不少依然活跃在世界文坛。在他们哀叹书店已不复往日辉煌的数年后,实体书店更是在网络书店的紧逼下步步败退。面对如此境况,他们又会怎样抒写对书店的情感?比如,对莱内尔书店念念不忘的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又会怎样评价直接删除了让读者浏览书籍这种神圣习惯的网络书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