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凯波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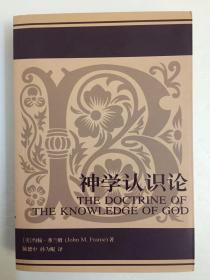 |
亚伯拉罕·凯波尔(1837年 ~ 1920年),出生于荷兰的马斯流,父亲是改革宗教会的一位牧师。在莱顿大学取得了神学学士和神学博士学位后,他自己也成为改革宗的牧师。
牧师,新教[1]多数宗派中的主要教职人员。拉丁文作pastor(牧羊人)。《新约[2]》中以牧人喻耶稣,以羊群喻教徒,所以新教用牧师称呼主持教务和管理教徒的教牧人员。
目录
人物简介
二十九岁、单身的凯波尔当牧师之后,才从自己牧养的乡村农夫身上对比,看出自己并没有得救恩之道,从而真正悔改归正。
看到现代社会碎片化的危机,他进入多个领域,身兼记者、报纸创始人、神学家、社会活动家、批判家、大学创始人、宗派创始人、政治家、党派创始人和荷兰首相(1901-1905)数职,他一生致力于用正统基督教信仰真理回应现代主义在各个领域中的各种公共思潮及谬误。
他61岁(1901年)第一次应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B.B.华菲尔德(B.B.Warfield)的邀请访问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磐石”讲座一时轰动,直到今天仍影响到很多年轻人。普林斯顿大学给他授予法学荣誉博士学位。
他活到83岁,生前常需要四位秘书,在一张办公桌前同时快速记录下他踱步时对四个不同问题的论述笔录。他用荷兰文写的著作汗牛充栋,直到今天还正在被翻译成英文(阿克顿研究中心的“凯波尔翻译计划”)。
在当代一些基督教思想家中,很多人例如薛华、范泰尔、普兰丁格、沃特思托夫、提莫太凯乐、寇尔森等,都称凯波尔是自己的思想导师。凯波尔传统也孕育了北美很多高质量的基督教文理学院,如加尔文大学、多特大学、救赎主大学、圣约大学、凯波尔大学等。
教会史权威马斯登教授曾说,凯波尔主义在北美福音派中的确传播得很成功。富勒神学院前院长理查德茅也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凯波尔时刻”——在经历基要派信仰从公共话语退却的失败之后,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基督教信仰需要一种公共视野和公共分析能力,来在思想界的公共生活中作光作盐。
出人意料的“归正”
凯波尔自己曾说过,“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扎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轨迹中,就是我们在心灵和生活中所经历的。”因此,认识一个人的思想,我们必须了解他的人生。
凯波尔的父亲是一位荷兰归正牧师,不喜欢教会里的激进派,一生致力于促进教会合一,也具有福音派人士的热忱。凯波尔在教会中长大,但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特别厌恶“那种基督教”,因为它已经变得空洞没有活力,在各种道德问题上,配不上代表一种真理的信仰。同时,他也厌恶教会里一种“虚假的保守主义”,对当代思潮只会一棒子打死,而不花时间去了解别人在说什么。
凯波尔是一个拥有惊人的脑力的人。从他的肖像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大脑袋)。幼年的凯波尔是他父亲在家教育培养出来的。他直到中学阶段才在雷登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后进入雷登大学,专攻文学、哲学和神学。他回顾这段教育经历时说,自己在很多当代圣经批判的思想中,并没有能力体察它们的谬误在哪里。这让他心中一直有个空洞:“我的信心无法深入扎根在我那颗未归信、自我为中心的灵魂中,在怀疑精神的炙烤下,必定会枯萎掉。”他在博士论文中将加尔文与一位自由派神学家Jan Laski相比较,表明自己比较喜爱后者。所有人都不能逃避自己时代的限制,凯波尔受教育的这段时间,正是历史批判在欧洲学府占据高地的时期,他的导师是自由派神学在荷兰的倡导者。他自己也将这段研读神学的时期,称为自己人生“未归信”的阶段。
二十五岁时,他接受一间教会的呼召,在荷兰一个名叫Beesd的小镇担任牧师。一开始,凯波尔认为自己的会众(大多是农夫农妇)都属于一种僵硬的正统派。但当他开始认识这些人、进入他们的每日生活时,会众对属灵事物的深度兴趣、对圣经的知识、对一种整全世界观的把握和他们对上帝恩典之主权的百分百肯定,深深触动了凯波尔。他此前并没有接触过这样一群人。他一开始觉得很遗憾,这样一群人好像还是被锁在宗教改革时期,他们无力回应现代社会的问题。
这段牧会经历让凯波尔回头钻研加尔文,在重读这位改教者对自己时代的回应时,凯波尔开始获得一种新的使命感:如果说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系统思潮,那么教会就有责任作出系统性的回应。如果像加尔文所说,教会是信徒之母,那么教会就又责任系统地牧养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信徒,在自己发挥恩赐的领域回应,而不只是退避到敬虔的一个角落,或试图回到过去某个敬虔的时代。
这个农村小教会的确成为凯波尔的灵性之母,可能也是这个起点让他后来成为教会的神学家(a theologian of the church),而不是学院派的神学家。
爱妻的影响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与此同时,把凯波尔拉回正统信仰的人,是他那位刚做过信仰告白、没有什么学识的年轻未婚妻。凯波尔在回忆录中写到,是妻子送给他读的一本英国小说《瑞德克里夫的继承人》,让他的心灵开始回家了。
故事中两位主角的经历、在葬礼前的悔改,让凯波尔仿佛身临其境。男女主人公在恋爱中因控制欲带来的痛苦挣扎,也让年轻的凯波尔正视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罪。最后他说,“当主人公菲利普跪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也正合手跪在我的椅子面前。噢,那一刻我灵魂里经历的事,是我后来才完全明白的。但是,从那时起,我鄙视我此前爱慕的,开始渴求我此前所鄙视的。”他灵魂的锚,在那一晚抛在了一个稳固的磐石上。
凯波尔对妻子的爱慕有加,他们结婚后一起养育了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批判自由派的内行
作为一个前自由派,凯波尔对现代主义思潮带出一种同情的理解,但这并没有阻碍他更加犀利地批判它。他指出,自由派神学是被一种对现实的肤浅认识蒙蔽,而失去了对上帝、祷告、罪和教会等更加现实之事物的认定。
在凯波尔看来,深受泛神论和演化论影响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是必然会产生的。他在批判时公允地与尼采等思想家对话,犀利地揭示出现代理论中的虚无和伦理谬误。他的文化批判致力于揭示出当代各种精神现象的本质。
尽管凯波尔持有一种“高圣经观”(high view of the Bible),但他反对制造一种“圣经崇拜(Bibliolatry)”。他将启示与默示进行了区分(成文的圣经是上帝的“默示”,而“启示”包括上帝持续向人揭示自己)。他反对一些圣经批判,但却不是一个字意派的基要主义者,因为释经要考虑到圣经作者使用的文体等因素。
凯波尔的作品将正统教义、对社会的分析和敬虔的激情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凯波尔传统全景》一书的作者在开篇就引用现代凯波尔神学权威John Bolt的话说:“你不能平平淡淡地介绍凯波尔,他的思想决不允许你这样做!”为辩明真理、建造教会的热心,从凯波尔的文字中涌流出来。
灵性是神学研究的根基
凯波尔的一生可以见证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4-25节所说的:“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凯波尔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三只小狐狸》,提醒基督徒要警惕智性主义和行动主义的危险,尽管他自己一生致力于这两项工作。他呼吁教会回归谦卑的灵性操练和诚实的学术讨论。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凯波尔和巴文克这样的大神学家的大部头著作中,很多篇幅仍是关于人在上帝面前之美好灵性的论述。
巴文克(1854-1921)比凯波尔年轻十七岁,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学,1902年接替凯波尔的神学教授之职。凯波尔在1880年建立这所大学时,希望它可以成为在各个学科建立归正思想的堡垒之地。人们常常把凯波尔和巴文克并列而谈,因为他们在思想传承上的确是近亲。巴文克常强调说,效法基督才是灵性生命的心脏。这两位神学大家为灵性神学注入了有力的内容,也警告那些嘴上号称“归正”的人,在实际生命中显出诚实、谦卑和恩典来。
诚实无伪的见证,会在一个人过世之后,仍长期发出馨香来。凯波尔只想做一个路标,指向基督。
参考文献
- ↑ 《世界宗教源流史》基督教之一百零一: 20世纪上半期的新教2,网易,2020-10-05
- ↑ 《文学回忆录》听与读 | 第五讲:新旧约的故事和涵义 ,搜狐,2017-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