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門(胡學文)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龍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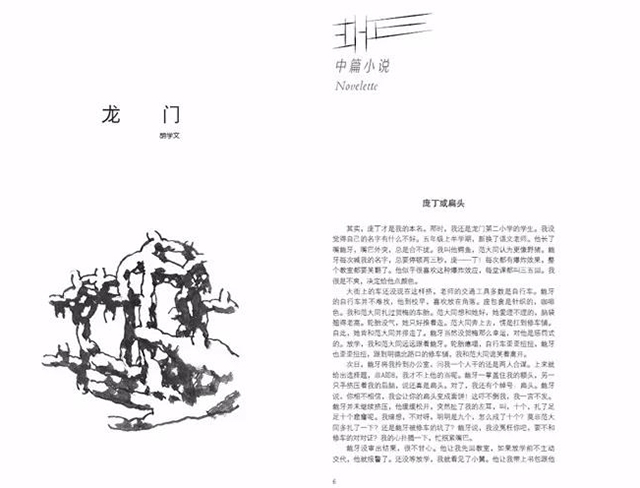 |
|
作者: 胡學文 體裁: 中篇小說 |
簡介
2019年8月,胡學文《龍門》榮獲第七屆花城文學獎中短篇小說獎。
胡學文:人物之小與人心之大
來源:《花城》微信公眾號 | 金赫楠 胡學文 2018年05月24日10:56
一
金赫楠:從2002 年的那篇《飛翔的女人》開始,我一直在閱讀你的小說。一路讀下來, 發現你的小說創作一直專注於那些生活在鄉村和小城鎮的人和事,村夫農婦、基層辦事員、個體小老闆等等都在你的小說中充當着主角。我想知道,你的寫作為什麼如此鍾情於這個人群?其實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有些擔心會對它不太以為然,這似乎是一個最最大路化、最最老套的問題。但我仍然想從這個問題開始我們的對話,因為在我看來,這關乎一個作家面對生活時候的興趣取向和情感趨向,甚至說得嚴重一些,這關乎一個作家的文學世界觀。
胡學文:其實我每次開始寫作的時候,腦子裡並沒關於人物「大」和「小」的明確概念,我只是在寫我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並不在意自己寫作對象的身份——雖然一個人肯定是有某種身份的,因為我覺得一旦進入寫作,身份不過是一件衣服,而我的小說想要觸摸到的是衣服包裹的人,與衣服無關,或者說不是衣服決定一切。我自己就是小人物,為什麼要寫大人物?當然,這和我的經歷不無關係,從童年、上學、參加工作到現在,我接觸最多,或者我身邊的人多是小人物,我沒有理由不寫他們。
當然,也不是說我就沒有接觸過別樣的個體和人群,近些年,我也接觸過官場中人、商場中人等等一些所謂似乎更高級一些的人,甚至還有親朋好友知道我在寫小說,時不時主動向我提供很多傳奇曲折的身邊故事,但這些人和事,卻總是引不起我太大的興趣,更沒有將他們寫進小說的願望。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興奮點或曰情感點,我的興奮點就一直停留在那一群人身上。我把它們稱之為「那一群人」,因為「小人物」這個概念是他人評定的,是從他們世俗意義上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上定義而來的。
如果一定要界定的話,我更願意稱自己的敘述對象「小人物」,而不是「底層」。因為總覺得底層兩個字似乎不能囊括小人物的全部,或者說給人的感覺是只有人之小,沒有心之大。從某種社會階層的劃分標準上看,他們是小,如果說我注意到這種小,同時我更注意小這層外衣包裹着的大,那種心的寬闊讓我着迷。而儘可能地去發現和呈現這種「小」之後的「大」,是我對自己小說寫作的期待和要求。
金赫楠:我倒是從未反感「底層敘事」這樣一個概念。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的衍生與發展從來都內含着對於事物的命名,文學的基本載體語言本身也是有命名性的。無論從文學史意義還是從理論批評意義上所命名的「底層文學」對於真正的創作又會有什麼損害或者妨礙嗎?重要的還是作家本身對於流行敘事腔調自覺地警惕與疏離。近些年來,底層生活和底層人物的確一直在以成為一個時髦的題材參與着當下的小說創作,曾經不同風格的作家們如今都來趕「 底層」這個趟,底層敘事正在成為不同風格、不同背景的作家表達自己文學意圖的萬能場景和母題。我個人的閱讀比較排斥的一種流行模式就是,拚命向讀者展示底層生活的困頓與無奈,展示他們因為身處底層所遭遇的物質匱乏與精神貧困,然後居高臨下地表達空洞蒼白的同情,試圖藉此升華出作者悲天憫人的精英姿態。血淚交織、「 站着幹活,跪着做人」等等這些的確是底層生活的一種真實,但是過分渲染一種真實,往往容易遮蔽和忽略另外一種真實。如果展示困頓、表達同情與憤怒成了底層敘事慣有的異口同聲,這個階層與人群在敘事中的形象僅僅定格在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那麼文學之於底層,沒有完成應有的承擔與責任。我一直在思考這麼一個問題,底層敘事中是不是根本就存在這樣一個悖論式的矛盾:真正身處底層的這些人們,囿於文化水平、資源占有、生存條件的種種局限,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機會來實現對自己生活的真實呈現以及對自己內心的準確表達。所以他們和他們的生活往往只能以人物和情節進入作家的創作,通過作家的敘事來呈現和表達。在這個過程當中,人和事就面臨着「被底層」、「被苦難」的可能。很多時候,即使那個作家原本來自底層,即使作家在情感上與他所書寫的人是相通的,但是,終究是有隔膜的。所以,我從文學作品裡面看到的底層世界永遠都是作家化了的底層世界。這是一個我自己現在也沒有想明白的問題,但是我相信,即使悖論無法超越,但是作家卻應該一直堅持超越的努力。
閱讀你的小說,我能明顯感覺到,你對人物充滿感情,知道體恤和心疼他們,更重要的是,你一直非常努力地去理解人物,這理解中包含着對人物的尊重。面對一個被傷害而又無力反抗的人,同情與憤怒都是很自然、很容易生髮的情感。這幾乎每個健康的人都能做到的。而作為一個作家,情感的能力應該更多樣、更深入。除了受苦遭罪之外, 你看到了小人物面對這些厄運時內心激發出來的反抗力量,那種躲在角落裡隱藏着的堅韌。
我想知道,你每每寫作的時候,都是從什麼視角、攜帶什麼樣的情感進入小人物的世界?你在寫作中怎樣規避被同時期的底層流行話語所裹挾?
胡學文:一位作家曾說,要貼着人物寫。我理解其含義一個是情感上的考慮,一個是敘事的策略。貼着人物,能觸摸到人物的體溫、心臟的跳動、情緒的起伏。言簡意賅,此話甚好。但我覺得,進入人物會有另一種奇妙。作者在創作時完全進入那個人物,成為那個人物。我寫《飛翔的女人》時,寫荷子在地上像水一樣流開,我就是荷子,那種無望擊穿身體的痛,我擺脫不掉。
我曾說過,「底層」這個詞沒有出現時,我關注的就是那些人,或謂之小人物。當底層流行時,我筆下的人物生活中的地位和身份沒有變。當底層被某些批評家詬病時,我筆下的人物仍是邊緣群體。這沒辦法,除非我不寫作。我不因底層敘事熱覺得趕上了潮流而沾沾自喜,也不會因為批評家的批評而躲避、苦惱。那和我沒關係,我說過進入到作品中,人物沒大小之分,沒底層與高層之分。當然,我在寫作中也力圖避免被幾乎大眾化了的聲音覆蓋。比如苦難,底層有,但哪個群體的人沒有呢?形式不同罷了。我不迴避,但苦難並不是底層最突出的特徵,把苦難與底層劃等號是滑稽的,是某些人的想象。以至於許多作品為苦難而製造苦難。本來我不迴避,可面對蜂湧的苦難,我躲開了。再如貧困,也是過度的想象與製造。我在一個創作談中說:「鄉村這個詞一度與貧困聯繫在一起。今天,它已發生了細微卻堅硬的變化。貧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則顯得尤為突出。困惑、困苦、困難。盡你的想象,不管窮到什麼程度,總能適應,這種適應能力似乎與生俱來。面對困則沒有抵禦與適應的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鄉村茫然而無序。」同樣,如果困被更多的目光注視,我會躲開。
金赫楠:我們來談一談《一棵樹的生長方式》。它被評家提及的並不多,也許是因為它的整體調子並不符合當下流行的所謂底層敘事的主旋律。但作為一個讀者和研究者,我是很偏愛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姚洞洞遭受着命運最無情的壓迫,他的成長充滿着失意甚至屈辱。最終,被壓迫到最低點的姚洞洞開始了他對命運決絕的反抗。這種反抗從一開始就帶有一種報復情結,是精心策劃之後的機關算盡和步步為營;當他犧牲了自己甚至家人的日常幸福,當他把宿敵逼進了絕境,始自維持生存與挽回尊嚴的抗爭,最終淪為快意恩仇的惡作劇。
你之前和之後的大部分作品中,也都貫穿着小人物對於命運的抗爭,不論是麥子、丁大山那種沉默的堅韌,還是吳響、左石、羅盤那種一根筋式地執著,甚至荷子式的近乎瘋狂的歇斯底里,這些表面看上去刨根問底甚至有些極端的行為,都是隨性而發的,沒有什麼計劃性,且都是心存善念的,歇斯底里的背後不具有破壞性,最終目的也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當姚洞洞從一個受虐者變成一個施虐者,當始自生活需要的反抗和掙扎一步步變成他的生活本身,我們從姚洞洞身上看到了底層世界的另外一種性 格:一種狡黠、機巧,一種強大的忍耐力以及 隨之而來的巨大的爆發力。種種爆發本來是有合理性的,但是一旦偏執地走下去、也會 漸漸生出惡意與破壞性——我把它稱之為「反抗溢出」:溢出了它能夠控制的範圍,溢出了它原本的合理的價值。我很好奇的是, 作為這個人物的創作者,這裡面寄託了你對底層世界怎樣的思考?
胡學文:我的所有人物都來自身邊的生活。這篇小說來自我對童年鄉村生活的一次回望。姚洞洞,說實話,這也是我自己偏愛的一個人物。你的偏愛,我想還是來自評論家的興趣點,按你的話說,這個人物足夠複雜, 可以提供更多闡釋的空間,你關於姚洞洞的種種分析,有些的確也是我想表達的,有些卻是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當然,好小說其實就是作家與批評家共同最終完成的。在我看來,姚洞洞身上攜帶着一種鄉村智慧:在現實中,一個人不得不顧忌着什麼,比如地位卑微者,可能不敢大聲說笑,走路不敢直腰,眉眼不敢放肆,這也許是外界的重壓使然。但沒有什麼權力或重壓能深入其內心,至少還沒到那個程度,還保持着心的自由,智慧的綻放。而且,現實越是逼仄,那智慧越有光彩。在我生活的鄉村,就有這樣的人物。我對這種智慧充滿興趣,想要去探究它來自哪裡,會對人物和生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金赫楠:你筆下那麼多的反抗者,最後大都還是陷落在悲劇的結局裡,好像只有姚洞洞取得了勝利——畢竟,他漫長的復仇最後實現了。但是取得勝利的姚洞洞,並沒有得到自己預想當中的痛快淋漓,而是陷入了內心的恐懼與虛無。我的感覺就是,面對這個唯一「成功」的人物,你在敘事中沒有直接評判,而是字裡行間夾雜着質疑。對姚洞洞式反抗以及最終的所謂成功,你的態度是矛盾的。
胡學文:的確是矛盾的。我對姚洞洞的情感其實挺複雜的,他身上所體現的生存智慧吸引我,但是對這種智慧除了感嘆之外, 我也覺得似乎還應該有一種警惕。這可能也就是對你所說「溢出」的警惕。在實際的寫作中。這個人物被我給寫失控了,我本來想讓姚洞洞最後體面地站在那裡,可是,最為一個贏家,他失去了贏家的氣度。
金赫楠:人物自身的邏輯,戰勝了作家的主觀預設,寫小說往往就是這樣。不知道你是否留心,幾年來的底層寫作中,還有這樣一種傾向,那就是因為貧窮、因為困苦,因為容易受到來自外部的欺辱與傷害,所以身處底層的人在喪失了資源占有上的優勢之後,卻被作家們賦予了道德上的優越感。姚洞洞這個人物的塑造,對這種想當然的道德優越感也是一個挑戰。
胡學文:這還是屬於評論家的發現。我在寫作的時候,人物就是人物,他的性格也許很獨特,但也是混沌的,他的舉動是隨着性格而發生的。人物出來之後,任由評論家尋找和分析吧。
二
金赫楠:你的小人物譜系中有這樣一些人:老實得有些窩囊,善良得稍嫌軟弱,苛求平安的同時難免怯懦,渴望擺脫貧窮、卑賤的努力中附帶着個人主義,身處卑微庸常之中堅守着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在一次次的失望和傷害之後,主人公們仍就沒有泯滅自己內心深處的善良,沉默地,也是執拗地堅守着人生的道德底線,堅守着自己對理想生活的嚮往與努力。不過,這樣的人物性格,在你的小說中其實並不多。我看到更多的,是另外一幕幕來自弱者的強勢反抗。回頭看看, 你這些年的小說中,其實一直貫穿着一這樣幾個關鍵詞:刨根問底、一根筋、追尋。除了上述《飛翔的女人》《麥子的蓋頭》《命案高懸》《土炕與野草》《失耳》《像水一樣柔軟》《誰吃了我的麥子》《一個人和一條路》等等,以及最近的這篇《謊役》,在這些小說中,當人物遭遇到命運的殘酷時,都會迸發出一種與自身處境看似不相符的強大力量去進行抗爭,執著地、執拗地,以一根筋式的信念支撐着一種刨根問底的追尋到頭、堅持到底。而這些追尋和堅持又往往沿着相似的軌跡走進了相似的結局。
胡學文:「刨根問底」和「一根筋」,被貼上這樣的標籤,我基本上是不喜歡也不反對。對於閱讀小說的人來說,可能我的那些人物確實是一根筋,什麼事情都一竿子捅到底,非尋個水落石出不可。我不是有意為之, 就是寫着寫着人物和情節就成了這樣。非要仔細回想創作過程的話,我承認在寫作初期,這樣寫有敘事策略上的考慮,比較容易實現緊鑼密鼓的敘事節奏和跌宕起伏的情節相扣,人物性格也在情節的推進當中更鮮明。但是在後來的寫作中,就與敘事策略無關了。可能因為我喜歡有韌性的人,所以往往努力挖掘並放大了這種韌性,所以人物看起來都有一根筋。其實,每個人身上都有他自己堅守或者堅持的東西,人生不也就是一個不斷追尋的過程嗎?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追求,各種方式的追求,我只是因為自己的偏好而放大了其中的某一點。
金赫楠:大家都強調你這個一根筋,其實倒不是說它不好。這些人物,為當下文壇的敘事,貢獻了一種對於人物性格的發現與體恤。到這裡,我得插一句,因為突然意識到,其實劉好、馬兌這些看似沉默軟弱的人, 也不是一味逆來順受,他們的身上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原生態的質樸與善良,在磨難與艱辛面前,守住一份善良,心存一些溫厚,堅持一絲理想,這本身也是一種反抗——儘管這種反抗是以一種柔弱的方式表現出來的。這更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文明進步和發展的最內在的呼喚和堅實的基礎,是對殘酷現實看似軟弱其實內勁十足的長久抵抗。
回來再說這一根筋。對一直跟蹤你的創作進行閱讀的人來說,讀多了,會對這種刨根問底的追尋產生過分的熟悉感:那種不顧一切、不惜代價、不計後果的堅持與執拗,那種一根筋式的刨根問底,籠罩在胡學文多篇小說當中,以至於有段時間我看到你的新作時從情節到人物不免略有似曾相識之感。
胡學文:我不過是呈現了這種追尋的艱難。我是個悲觀的人,如果筆下的人和我一樣悲觀,不止是人物沒有出路,我也會絕望的。也許沒什麼結果,但在追尋的過程中,我讓人物也讓自己看到希望。這些年我在寫小說的時候確實越來越開始注重對心理的描寫。但是,其實我並不認為,注重人物內心的描寫就一定比關注人物的外部行為更高級。敘述的着力點側重於什麼地方,這是作家的喜好,也和寫作時的敘述內容和所選擇的敘事策略相關。寫人物的外部行為,比如動作、語言,其實仍然可以傳遞出人物的心理變化,很多時候這樣可能比直接寫心理更有難度,所謂「不着一字盡風流」。
金赫楠:我同意你關於寫外寫內的看法。不過,具體到你近些年的創作,我仍然認為「由外轉內」是一個突破和進步。還有一個發表在《中國作家》上的中篇《虬枝引》,初讀後我很是驚訝,一度還又翻回到首頁來再次確認作者是否為我所熟悉的胡學文。這是一個關於外出打工者歸鄉的故事,但是你寫得很魔幻——是的,我使用了這樣一個原本和你的創作不着邊際的詞語——魔幻:主人公喬風,一個外出打工的男人,回鄉與妻子商議離婚,卻在回鄉的路上發現自己的村莊消失了。於是他放下了原本回鄉的目的,一門心思地開始了對自己村莊的尋找與重建,但是最後一覺醒來,發現在那曾經熟悉的一切終究還是回不來了,他也因此只能永遠走在回鄉的路上卻回不到家了。
胡學文:評論家們總是認為我的小說很實,甚至是太實。雖然我並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好,卻也因此多少有了想要做些改變的躍躍欲試。不是都說我太「實」嗎?那我就寫一 個「虛」一點的。寫作這篇小說的時候,我其實是滿心蒼涼的,按你的話說,《虬枝引》無論使用了一個怎樣魔幻的架構,其創作靈感當然還是來自現實生活。你知道,我是從農村出來的,我身邊也有很多這樣來自鄉間、現居城市的親戚和老鄉,我發現每每提到自己現在住所的時候 ,他們的表述都不是「家」,只是說回什麼什麼地方去;而只有提到自己的鄉村或者鄉村所在的地域,才會使用「回家」這樣的詞。這種「虛」的確是我刻意追求刻意營造的,但我並不是隨便逮住一篇小說就迫不及待地「虛無」起來。是對故鄉的思考和對另外一種敘事策略的期待,碰撞出了這樣的一篇《虬枝引》。
沒有一個作家不想超越自己,問題是怎麼超越,是否能超越?也許自己認為超越了, 可那種超越並非有意義。但不改變是不行的。我不知道所做的努力會是什麼結果,方向也不是很明確,就像勘礦一樣,這兒測測, 那兒試試。
刊載於《小說評論》2014年第5期
參考來源
- ↑ 胡學文:人物之小與人心之大--訪談--中國作家網 2018年5月24日 ▲胡學文新作《龍門》刊載於《花城》2018年第3期 胡學文:我的所有人物都來自身邊的生活。這篇小說來自我對童年鄉村生活的一次回望。姚洞洞,說實話,這也是我自己偏愛的一個人物。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