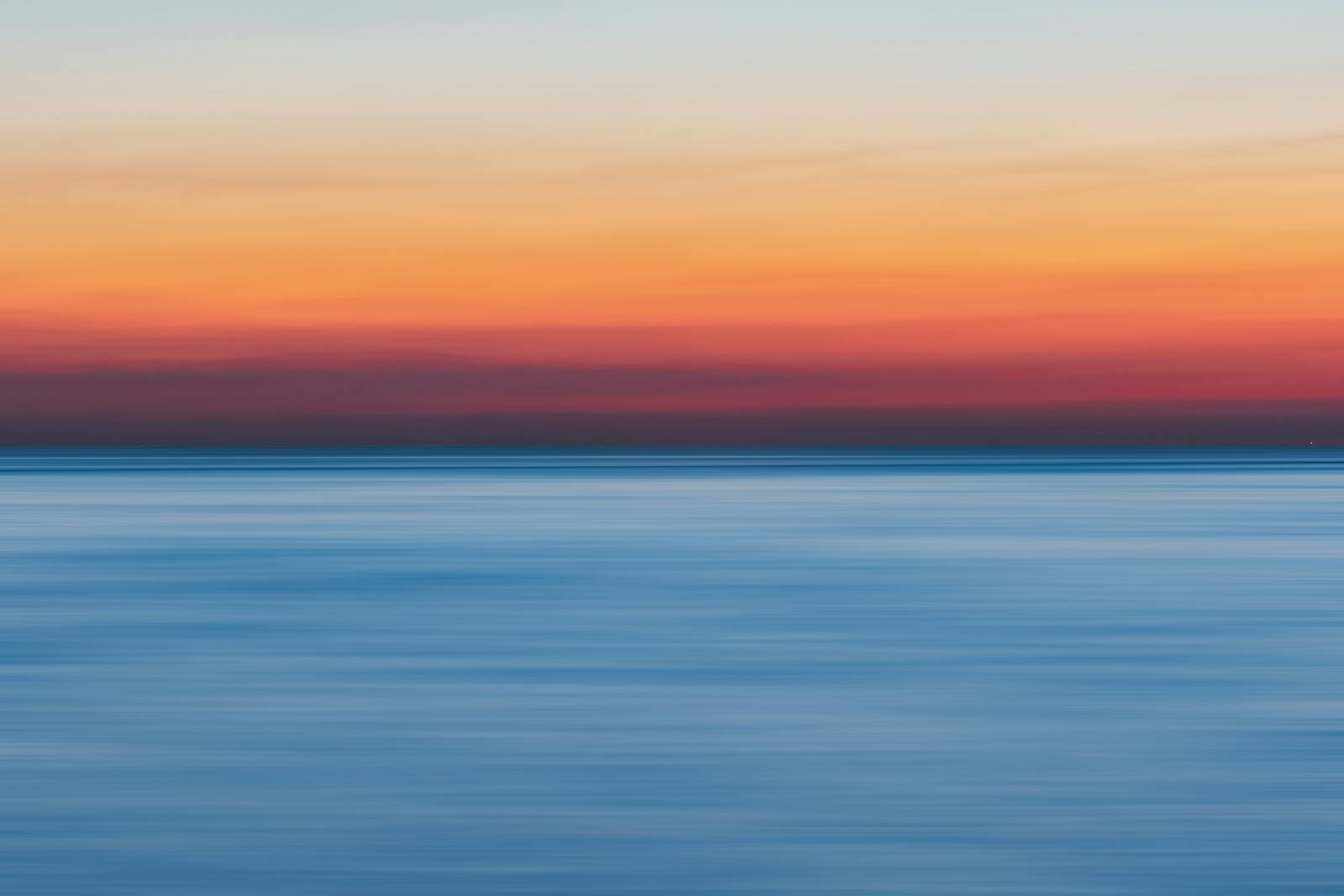還是那枚燭火(董玉明)
作品欣賞
還是那枚燭火
忽然停電了,黑暗像蝴蝶一般悄無聲息地飄落下來。心跳趨於平緩,我試着凝視這個虛假而又真實的世界,描摹着壁燈、書架、筆筒、方桌的形狀,仿佛我正睜大一雙慧眼,與這個浮塵四起的世界直面對視。
我在想,如果人一輩子都生活在黑暗之中,會怎麼樣呢?於是,我遠遠地望見了一枚燭火——一枚在我二十歲時由一個女孩點燃的微弱而跳動的燭火。
停電,當時對於我家那幢舊式住宅是習以為常的事,正因如此,我生活的某一階段總是陰霾交織,甚至黯然無光的。狹窄的四壁和壓抑的空間,剛好能將我隱藏起來,頂棚低矮,經年的潮濕在牆壁上留下氤氳的斑點。窗子外是一堵牆,牆外是一條南北通暢的小馬路,小馬路盡頭就是一處繁華的街道,但喧囂的市聲與光怪陸離的色彩距離我的小屋相當遙遠。
寂寞的二十歲啊,我常常坐在冰冷堅硬的板床上,守望着黑暗,幻想着莫名中墜落的飄雪,能打濕我焦灼而浮躁的心。這時,小雨出現了。
在那之前,一本油印的《小青島》雜誌上選登了我的一首短詩《死屋》,刊物是自費油印的,在朋友圈中小範圍傳閱着,偶然被小雨發現了,於是她無意間讀到我的詩,於是她打聽到我的住處,於是她輕輕扣開了我銹滿塵跡的家門。
小雨說她只是想當着作者的面把詩默念一遍,小雨說她很想知道詩中的意象究竟是什麼意思,小雨說她很愛讀那些分行排列的文字。
當我緊張地找到她那雙淒楚柔弱的眼睛時,才發現,那裡面已經是浸滿淚水了。
不久,小雨再一次敲開了我的家門。
不久,我們相愛了。
半月後的一天傍晚,小雨一臉倦容地出現在我的老屋裡,她的臉色慘白,目光呆滯,紅腫的嘴角還殘留着一絲血跡。我正在猶疑間,她已經樹葉般無助地撲到我的懷中,她抽泣着,溫潤的淚水打濕了我的衣襟。停了一會,小雨哽咽地為我講述了一個故事。
一個天生孱弱的女孩,在尚不明事理的時候,因為父母離異遠離了故鄉,她被輾轉着送給了別人。女孩在驚恐與期盼中慢慢長大,長到應該考取大學應該養家的年齡,繼母強迫她放棄了學業,並把發生在女孩身上的故事告訴了她,繼母唯一的要求就是,到了償還舊債的時候了,二十年的養育之恩,至少應該用十萬元的價錢來回報,而且還要加倍地償還。女孩一直受着繼母的打罵,無端地指責,無理地嘲弄,無盡地侮辱,加上繼母以死相逼的威脅……
女孩就是小雨,在她如泣如訴的話語中,我聽到源於她心底的聲音,我們緊握的雙手緊靠的雙臂一直在顫抖。
我知道所有的勸導都無以安撫小雨那顆傷痕累累的心,沉默,只有沉默。幾乎是出於上天的安排,忽然,停電了,黑暗像霧一樣籠罩下來,四周靜靜的,只剩下怦然的心跳和緊張的喘息聲。終於,在靈魂的牽引下,我們找到了彼此矚望的眼睛。
她的長髮在我的指尖上游移,她的臉深埋進我的臂彎。她沉靜地說:「我永遠也不離開你啦,今晚,我要把一切都給你。」我被一個神聖的近乎沉重的意念遠遠地操縱着,像一個空虛的沒有意識的木頭。我把小雨安置在板床的裡面,然後點起一支煙,看火頭一明一暗地隱現,看煙霧一起一伏地升騰。
小雨的聲音在空曠的四壁中飄來盪去,仿佛在無始無終地描摹着一個愛情的童話。終於,小雨緘默不語了。她的手從我的肩頭滑落下去,不知何時,從角落裡摸出一支紅燭,「嚓」地點燃了,火苗由弱到強,愈來愈亮,照見了她披散開的頭髮,深含不露的眼眸,緊閉着的嘴唇,敞開的碎花衣領……鮮紅的燭淚滴淌下來,兩個單薄虛幻的人影在牆上移動,我們寂然無聲,她就這樣陪我坐着,仿佛世間一切言語都失去了意義,仿佛時間凝固下來,悄悄地結成了冰。
等到天光曦微,白晝來臨,等到燭火熄滅,長夜不再,小雨就在我黯然的眼光中,披着一身的疲倦和淒楚,匆匆地離去了。
沒過多久,我就去了遠在瀋陽的遼寧文學院。
想來,我不是對光明與黑暗天性敏感、甚至有所苛求的人,然而,每每在生命突然出現短暫的變故時,我都無力拒絕往昔及未來的誘惑,而我永遠不能把握住一種伸手可及的現實。我不確定從幼稚到成熟有一個本質的界線,事實上,正是許多個猝不及防的瞬間,讓人產生了長大了成熟了的疑惑。
感謝生命,讓我為一段平凡的故事,平添了美麗而凝重的愛意。感謝生命,讓我沒有為倉促的青春,勾勒一個索然蕭瑟的結局。所以,在陽光普照的日子裡,我也會偶爾弄滅所有的光亮,讓思念與自責回到那個燭光跳躍的夜晚,穿越夢境,抵達那個永無昨日的彼岸。
誰也無法預言明天,就像誰也無法重現過去,所以,在一枚燭火的舞蹈中,我們應該學會感謝今天。 [1]
作者簡介
董玉明,筆名方程,男,69年生人,原在某醫院工作,80年代初開始創作,98年因病雙目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