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蜂人與花(周海)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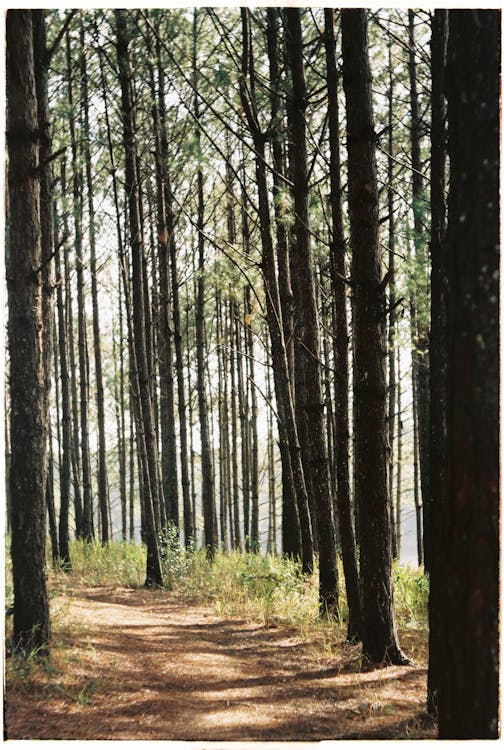 |
《放蜂人與花》是中國當代作家周海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放蜂人與花
每年,都有放蜂人來到我們村。放蜂人的使命就是用一生的時光追逐鮮花。從春天開始,他們攜帶蜂群,從南向北開始一場遷徙。到我們村,正是紅花草開花的時候。在早春還帶有一些寒意的風中,最先綻放的就是紅花草。放蜂人打開蜂箱的門,蜜蜂們嚶嚶嗡嗡地飛舞在稻田裡,還有幾分蕭索的稻田一下子就熱鬧起來了。
沒有人拿紅花草當花。本來,紅花草就是肥料(綠肥),插秧之前,就要將稻田裡開得正盛的紅花草犁掉。可是對放蜂人就不同了。紫雲英蜜是最好的蜂蜜之一。爺爺有便秘的老毛病。每當大便不通暢的時候,他就會沖一杯紫雲英蜜,也給我沖一杯。而我在多年之後,才知道聽上去詩意盎然的紫雲英就是紅花草。放蜂人將家安置在離稻田不遠的樺樹林子邊。樺樹林下面就是干灘,接近水源,雨天樺樹茂密的樹葉又可以遮風擋雨,確實是一個臨時安家的好地方。他們搭起帳篷,支起灶台。當炊煙升起的時候,女人在竹竿上晾衣服,他們的孩子安靜地坐在凸起的樹根上,看家狗在門前歡快地跑來跑去,這就像一個家的樣子了。
這一家三口的放蜂人已是村莊的熟客了。年年這個時間,一匹白色的母馬拉着一輛橡膠輪胎的碩大無比的木板車,咯吱咯吱地行駛在村邊的砂石路上,所有的家當包括蜂箱都在車上。可是,好多年過去了,放蜂人不見老,他的女人也不見老,只有那匹白色的母馬鬃毛不斷地掉落,和我們差不多年齡的孩子個頭漸漸長高。剛開始來的時候,他們一口的南方方言我們一句也聽不懂,在一陣比比劃劃之中,才知道他們看上了我們地里的花。這對於我們來說是求之不得的事,甚至有些喜出望外。將要犁到地里的綠肥居然能換來蜂蜜,誰不高興呢!放蜂人,我們都這麼叫—準確地說,是這家放蜂人的家長,這個沉默寡言的、身材瘦小的男人,和我們村商定好,每個月按照一定的比例上繳收穫的蜂蜜。有田的人家就能免費品嘗到美味的蜂蜜。不捨得吃的,還可以拿到街上賣,價錢自然極便宜,沒有田地的公家人也能以青菜的價格買到蜂蜜。這樣,幾乎全村子裡的人都有蜂蜜吃了。
儘管放蜂人與我們村形成了某種默契,漸漸融入我們的生活,但他們一家的南方口音、身材、穿着甚至眼神,還有帶來的白色的母馬、蜂群、帳篷,無不打上了異鄉人的標記,像從遙遠的世界飄過來的一朵白雲。我們只知道,他們是放蜂的。就像村里人放水牛為了耕田,放奶牛為了擠奶一樣,他們放蜂是為了收穫蜂蜜。放蜂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大到油鹽醬醋小到針頭線腦都要到村子裡購買。放蜂人的女人身材嬌小,皮膚白皙,裝束普通,每天早上一樣提着籃子上街。可是無論上早市的人群多麼擁擠,大家都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認出她。她努力地學習、模仿我們的說話的口音,以便和菜販子討價還價時溝通順暢。可是因為怎麼也改不掉的口音,反而把我們的話說成不知哪兒人說的話了。於是有人笑她「山東的驢子學馬叫」,她雖然不能完全聽懂,但是看着村里人善意的揶揄的神情,頓時疏離感陣陣襲來,白皙的臉上泛起一層紅暈。
就在放蜂人的馬車車輪的咯吱咯吱聲響起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興奮不已,因為吃蜂蜜的日子就要來了。他們帶來了南方的氣息,陌生而又溫暖。比方說,我們的棉襖還沒有脫掉,他們只穿着一件單薄的毛衣。白色的母馬的鬃毛像一匹緞子,兩隻眼睛水汪汪的能照見人影。他們在樺樹林子邊搭帳篷的時候,我們就在一邊好奇地看着,看着他們別樣的生活。而他們大概已經習慣了這些,視若無人地做着手頭的活。巨大無比(在我們看來)的蘑菇似的帳篷變魔術似的搭起來了,母馬栓在樹邊,啃着地上剛剛返青的草,黑白相間的花狗不再朝我們吠叫,趴在帳篷前睡覺,蜂箱圍繞着帳篷一層層地摞起來,就像一道圍牆。只有他們的孩子,用一種怯生生而又有幾分討好的眼神看着我們。
很快,我們就和放蜂人的孩子成了朋友,玩到一起去了。本來,一句話、一個玩具就可以讓孩子們成為朋友,何況他們家還給村莊帶來了蜂蜜。最重要的是,他學起我們村的話特別快。沒用多久時間,單聽他說話,會誤以為他就是我們村的人。他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只記得我們給他起的外號「黃毛」,因為他的頭髮又稀疏又有些泛黃。放蜂、餵蜂、繁殖、割膠之類的大活放蜂人自己親自動手干,黃毛只在一旁打打下手。即便如此,黃毛有關於蜜蜂的知識仍讓我們欽佩不已,比如蜜蜂分為蜂王、雄蜂與工蜂,只有工蜂才承擔採集花粉釀蜜的工作,而壽命只有短短的兩三個月。工蜂在蜂箱內為體型最大的蜂王建造宮殿一樣的王台,蜂王在王台內坐享其成、繁殖後代。黃毛帶着一些神秘的神情,小聲告訴我們:工蜂每天飛來飛去的路程加起來有一百多里路!一百多里,比從我們村到縣城還要遠呢!我們毫不懷疑,黃毛將來一定是一個優秀的放蜂人。
環繞村莊的是無邊無際的長長方方或不規則形狀的稻田,在四季里變換着屬於它的顏色。現在,紅花草給稻田鋪上了一層殷紅色的毯子。環繞村莊的,就是一層一層的殷紅色,有幾分喜慶、吉祥,雖然春風還有幾分凜冽。「一隻小蜜蜂呀,飛在花叢中呀,飛呀,飛呀.......」小蜜蜂從樺樹林子飛到稻田,又從稻田飛回樺樹林子,完成它短短的一生的使命。在帳篷前,飛舞着成千上萬隻完成采粉任務的歸巢的蜜蜂,簡直要將帳篷前的一方天空占滿了。放蜂人渾身上下都粘滿了蜜蜂,看起來好像穿了一件用蜜蜂綴成的衣服。而放蜂人視若不見,有條不紊地干着自己的活。我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幾乎每個人都被蜜蜂蜇過,臉上、頭上、胳膊上鼓起一個個紅色的腫包。放蜂人將蜂蜜塗在腫包上,腫包不痛了,要不了一會兒,腫包漸漸消失了。
後來我們才知道,蜜蜂用尾刺一蜇,它的生命也就結束了。而我們為了嘗到香甜的蜂蜜,有時會故意去招惹蜜蜂,引它將尾刺蜇在我們的胳膊上、手上。然後,我們悄悄地在一邊舔着放蜂人塗在我們胳膊上手上的蜂蜜。黃毛自然是知道的,但他很意氣地裝作不知道,任由我們殺死他們家一隻又一隻的蜜蜂。也許,是他們家的蜂王繁殖能力太強了。因為,我們從未見他們家的蜜蜂少過。每次去樺樹林子,仍是成千上萬隻的蜜蜂飛舞在帳篷前的一方天空。放蜂人穿着蜜蜂綴成的衣服,有條不紊地干自己的活........日子過去了,春風裡有一股一股的水汽,溫暖的氣息襲來,紅花草也即將要犁掉了。漸漸地,每戶人家的櫥櫃裡都有一瓶深黃色的蜂蜜。為了防止小孩一下子將蜂蜜偷吃完了,櫥櫃還上了一把鐵鎖。櫥櫃裡有沒有一瓶蜂蜜,還是不一樣的。好像有了這一瓶蜂蜜,日子過得就有些甜。誰不願意過甜日子呢。放蜂人有時候也將蜂蜜拿到鎮上去買,鎮上賣得快一些,價錢也貴一些。趕廟會的時候,放蜂人的蜂蜜賣得特別快。最後,他會留下一點,交給做糖人的手藝人。我們眼看着手藝人玩魔術似的將蜂蜜熬成一個個形狀各異的糖人。回來的路上,我們每個人手上拿着一個竹棒糖人,它的香甜的氣息經久不散。
插秧之前,所有的紅花草都犁掉了。放蜂人不走,他在等油菜花開。在這之前,他要用儲存的蜂蜜餵養蜜蜂。帳篷的角落裡,摞着一隻比水桶略小的塑料桶,裡面裝滿了金黃色的蜂蜜。這是放蜂人的身家性命,誰也不敢動,黃毛也不敢動。沒有了它,花源不足的蜜蜂就會餓死。在等待油菜花開的日子裡,除了一天數次打開蜂箱餵食蜜蜂,放蜂人和蜂箱裡的蜜蜂一樣,沉入一種短暫的歇息狀態。放蜂人也許是習慣甚至享受這種狀態,他常常靠在帳篷前的樹樁上抽和煙農換來的黃煙,沉默、悠閒地望着樺樹林上方的天空。女人還是在忙她的家務,她好像特別喜歡去樺樹林邊的干灘里洗衣服。白色的母馬吃飽了春天的多汁的嫩草,看起來像一匹駿馬的樣子了,好像跨上去它就會飛馳遠方。花狗一見我們來就搖頭擺尾,撲上來舔我們的手。黃毛每時每刻都在期待我們的到來。春天的樺樹林子,有小小的紫色的野花,有蠶豆大小的野草莓,有一群一群忽來忽去的白蝴蝶,岸灘的泥地里,隨便挖一挖,就有剛灌漿的鮮嫩的葛根.........寂寞的樺樹林子不再寂寞。玩累了,我們也靠在樹樁上,沉默地望着樺樹林上方的天空。
等不了多久,油菜花就開了。油菜花長得快,開得猛。有時候頭天油菜花才打着花苞,第二天一早醒來,漫山遍野都是金黃色的油菜花。村子裡的人不捨得大面積地種油菜花,收穫的不多的菜籽要送到油坊,榨出來的油炒雪裡蕻,剩下來的留着過年炸山粉圓子。即便如此,在稻田裡、菜地里乃至山腳下的荒地里插種的油菜花一旦齊齊開花,還是給人一種鋪天蓋地的感覺。天氣一天比一天暖和,樺樹林子又熱鬧起來了。「一隻小蜜蜂呀,飛在花叢中呀,飛呀,飛呀.......」經過短暫休整的蜜蜂跳着八字舞,更加勤快地採集油菜花的花粉,好像要將荒廢的時光彌補回來。它們的翅膀扇動的嚶嚶嗡嗡的聲音在空氣中傳遞,村子裡每個人似乎耳邊都迴響着這種聲音。這是一種美妙的聲音。很快,我們就要嘗到香甜的油菜花蜜。每戶人家的櫥櫃裡都會多出一瓶油菜花蜜,柜子還是會上一把鐵鎖。而我們也將最先在胳膊上手上品嘗到香甜的油菜花蜜。
油菜花花期短。油菜花謝了的時候,放蜂人一家就要走了。他們要趕去和北方的鮮花會面。其實這時候,村子裡還有幾棵槐樹正在開花,田埂邊和山腳下更是野花遍地。村裡的女孩常常去山腳下采映山紅,抱在胸前的映山紅將她們的臉映得紅撲撲的。可是,黃毛說他爸爸嫌花源太雜,會攪亂蜜蜂的胃口和食性。在溫暖的日子裡,放蜂人觀察、判斷天氣狀況,開始整備行裝,做出發的準備。他們將一路向北,北方有我們想象里才有的平原、戈壁、大漠、綠洲、草原......那兒的鮮花在不同的氣候和節氣里次第開放,迎接着放蜂人。這是他們早就商定好的默契的約會,年年如此。據說,他們最遠將到達新疆。當他們到達的時候,那兒的油菜花會將所有的金黃奉獻給遠來赴約的放蜂人。
在一個空氣清新、充滿野花芬芳氣息的清晨,放蜂人一家駕着馬車上路了。我們站在村邊的砂石路上,看着馬車從我們面前經過。我們齊齊望着黃毛,坐在馬車上的黃毛只用一種很漠然的眼神看着我們,然後抱起膝蓋裝着沒看見我們似的望着天空。我們憤怒了。他一定以為我們是來討還借他玩的鐵環、陀螺。怎麼會呢,我們是朋友,何況我們還嘗了那麼多回他們家的蜂蜜。是的,他是習慣離別的,北方有次第開放的鮮花,也很快就會有新的朋友。不知誰說:「吐他口水!」可是馬車已經駛遠了,我們只能將口水吐在馬車的車轍上。第二年,在早春寒冷的天氣里,還是紅花草先開出一片殷紅。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來自南方的溫暖的氣息。可是,放蜂人沒有來,以後再也沒有來。有人說,他們回了溫暖的南方的老家,那兒花期很長。也有人說,是北方的鮮花把他們留在哪兒了。於是,有很多年輕人離開村莊。有人去了溫暖的南方,有人去了鮮花遲遲開放的北方。然而,他們再沒有回到村莊,所以也沒人知道放蜂人的信息。這其中也包括我。
我一直固執地認為:是遠方的鮮花把我們帶走的。[1]
作者簡介
周海,男,70後,安徽省樅陽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