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果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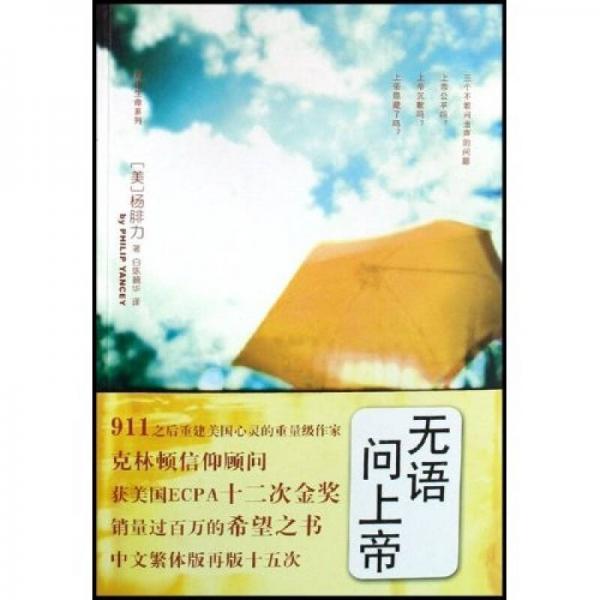 |
鄭果(1919 — 2009),普世華人教會著名傳道人、牧者。華人差傳事工推動者,參與、鼓勵華人教會從事宣教達50餘年之久。
傳教士(missionary),亦叫作宣教師或宣教士,是堅定地信仰宗教[1],並且遠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們傳播宗教的修道者。雖然有些宗教,如日本神道教,很少會到處傳播自己的信仰,但是有很多宗教用傳教士來擴散它的影響,例如伊斯蘭教與基督宗教[2]。
簡介
一、早年背景
鄭果於1919年生於福建省漳平市和春村,父親鄭琛原是佃農,藉著殷勤耕作、打散工,還清債務,並且存有積蓄可以在縣城開店鋪作小生意。鄭琛共有8個子女,鄭果在家排行老五,原名「永善」,是其私塾老師鄭雅翁所取的名,獻身後改名為「果」。因早年家境艱困,從進私塾到到15歲才完成小學。後經自己努力,考入縣城初級師範學校,畢業後分配到當地的一間初級小學當校長。但其心仍不滿足,續又考入福建省高級師範學校。不久抗戰爆發,學校由福州遷到永安。在學期間,他與同窗組織抗日後援隊、抗日宣傳隊,專門對付奸商與漢奸,是一位愛國的熱血青年。高師畢業後,他留在永安縣菁城中心小學擔任校長,期間並參與漳平縣中學的籌備與擔任該中學的國文、歷史、地理老師。
抗戰勝利後鄭果參加縣議員的選舉,於1946年當選,年僅26歲。不久又被選為縣議會議長。任內,他設立了電燈廠,並將九龍江流經漳平縣城的碼頭修復,造福一方百姓。
在縣議會工作期間,鄭果所任用的一位幹事,名叫戴明星,是位基督徒。他常邀請鄭果去禮拜堂聽道。如此大約過了數月到一年,在教會牧師的鼓勵下,鄭果雖然在信仰上尚不夠清楚,但還是接受了洗禮(1946年)。第二年就被選為執事,但那時他只是一個沒有重生得救的、掛名的基督徒而已。
鄭果的重生是在教會所舉辦的一次培靈大會上。當時,一位由廈門來的女傳道,在連續幾個晚上的講道中,根據約翰福音第三章,著重傳講「重生的真理」,句句話都打動鄭果的心,於是他真誠認罪悔改,接受主耶穌住在他的心靈中。從那日起,他在言語和行為上,有了很大的改變。
重生以後,鄭果愛慕神的話,喜歡正常的靈修生活,每逢主日不僅自己去教堂敬拜神,還常常邀約朋友們同去。隨著愛主的心增加,主也將愛人靈魂的心放在他心裏。他開始關心其家鄉和春村幾十戶人家靈魂的得救。每主日上午,他在縣城禮拜堂聚會,下午則回鄉下去傳福音。
那時鄭果雖然身為縣議會議長,但逐漸覺得所做之事意義有限;加之他父親在61歲,岳母在50餘歲相繼辭世,更讓他感到人生苦短,仔細思考如何才能有意義地使用這短暫的人生。由此他覺悟到基督徒唯有「獻上自己」做「聖工」,才是有意義的人生。
1948年,鄭果內心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每逢讀經或聽道時,他都看到神的旨意是要他成為傳道人,讀經時讀到「主的差遣」、「救人靈魂」、「莊稼已熟」等經文時,就深受觸動;聽道時,一聽到工場的需要、神需要工人,耳朵就開通,心眼就看見。因此他已經清楚神的呼召,願意為主獻身了。1949年,鄭果專心尋求神的帶領。有一夜,在半睡狀態中,他聽到神的聲音說:「我已揀選你,也要使用你,你現在可以去讀福州神學院。」 醒來之後他懷疑神對他的指示,因為當時中國政局已發生改變,無神論當道。後來他藉著希伯來書十一章,得到了神的確認,因此除去心中的懷疑,決定奉獻自己去讀神學。這時,另一個實際問題又臨到他,那就是他事奉神以後,他一家六口今後的生活怎麼辦?鄭果家中並無積蓄,因此他又再次的求問神。神就賜他一句話:「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33) 。既有神的話,他就決定前行,把兒女交給妻子陳懷民,並將神所賜的經文傳給她。他的妻子也是在他歸主數月後信主的,是一位有信心的女人。在接受了神的話以後,她就叫丈夫安心去讀神學院,家中的事交給她,她會倚靠主而過活。
妻子既與他同心,在獻身的道路上支持他,因此他於1950年初就辭別了妻兒,離開家鄉,入讀福州協和神學院。他很快就適應了神學院有規律的學習生活,刻苦研讀聖經,練習講道,有時也去醫院探訪病人。當時神學院院長是林光榮,[1] 教授多數是留美的,有教學之專長,但少數受到「自由派」神學思想的影響,與純正的福音信仰有很大出入,以致在同學們中間造成許多的混亂。加之神學院在共產黨政權下,受到諸多監管和限制,有些信仰幼嫩的同學,經不起挑戰與打擊,就放棄信主的心。但當中也有許多信心堅定的同學,站穩立場,為真理作出美好的見證。在這種情況下,鄭果再次尋求神給他引領。不久,神藉著華北神學院一位畢業生指示他說:「國內的神學院都關門了,你還是跟我去香港讀神學吧。」 鄭果以此為神的指示,就決定前往香港繼續接受神學裝備。
二、在香港
鄭果在去香港的路上,途經廣東的一個地方時,卻不料遭到扣押,被當地的檢查人員叫去問話,認為他需要接受無神教育,結果被判教育改造。在這段時間裡,生活極苦,每日兩餐吃不飽,過著「不知明天將如何」的恐怖生活。在起初的15天裡,他毫無喜樂,因為前途茫然,不知到何時能得到自由,心裡又惦記著家人。他只能藉背誦約翰福音3章16節與詩篇23篇來安定自己。他想念年老的母親、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女。因怕見不到他們,他就在夜深人靜時向神禱告說:「神阿!如果禰願意,讓我恢復自由,與家人團聚;不然,求禰看顧他們,相信禰看顧他們勝過我看顧他們。」 在接下來的15天,鄭果漸漸恢復正常,並且對主有信靠和順服的心了。在第30天的夜裡,他一連三次聽見聲音說:「四十五天期滿,要釋放你,並要你去海外做見證,」 因此他篤信不疑這是神向他說話。果然在第45天中午,鄭果被宣告自由了。
1951年3月,鄭果在廣州獲得通行證,然後搭乘火車到深圳,再經過羅湖橋到香港。後來靠著一位宣教士資助他的500元港幣,又在蘇佐揚師母的介紹下,鄭果才得以進入香港播道會所屬的播道神學院就讀。
鄭果因為信主比較遲,加上10年的工作,故當開始讀神學時,已經32歲。三年神學時光中,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聖經研讀上。他先後受教於鄭德音、桑安柱、胡恩德和滕近輝等良師,加上他自己渴慕追求的心,使他學業精進,也更加認識神,得著神。
1953年,鄭果完成神學院學業,這包括一年在福州協和神學院與三年在香港播道神學院。畢業後受聘留校擔任教員兼男生輔導員,這樣他又繼續在學校事奉六年(1953-1959),到他離開學院時,已經40歲了。
在學院工作期間,鄭果在中國大陸的妻子兒女曾向政府申請出國與他團聚,結果不但未獲批准,還被限制離開本鄉本省。此事不免使鄭果痛苦失望,只有仰望主的憐憫。
鄭果在香港事奉期間,非常渴慕得著屬靈的恩賜。有一天,他獨自一人在屋內禁食禱告,徹底的認罪,對付自己,倒空一切;又靜默在神面前,享受他的恩愛。忽然有大喜樂,感受到有力量進入他的心靈,使他唱歌讚美,他知道那是聖靈的工作,是主聽了他的禱告,成全他的心願。這次聖靈充滿的經歷,帶給他講道的恩賜和能力。之後他帶領了兩次聚會,先是崇真會聯會的夏令會,地點是在九龍西貢的樂育神學院。聖靈大大地作工,幾乎全場會眾都受到感動而流淚;有大約40人當場願意奉獻自己作傳道人,其中有張子華、張子江、以及劉承業等弟兄。另一次是港九禮賢會所舉辦的聯合夏令會,地點是在沙田。因著鄭果的講道與交通分享,聖靈再次動工,帶給禮賢會年輕人的屬靈復興,其中有在港大唸書的彭永福、文子方與一位陳姓的弟兄。為此鄭果深深認識到聖靈的工作。
在港期間,鄭果經常思念他的家人,包括雙親、妻子和兒女,多次懇求神帶領他們出來,但都沒有成功。他屢次求問神「為什麼?」 神卻一次又一次的要他學習順服。於是他每當思念親人肝腸寸斷之時,就在禱告中更為迫切地記念他們,同時也從神的話裡面得著慰藉。
在香港事奉期間,鄭果常常思考一個問題:西方教會都有差傳事奉,為何華人教會卻沒有差傳的工作? 是因為沒有人,還是因為沒有錢?父神因此就將這個負擔放在鄭果心裡,並且藉著三件事開啟他宣教的心。首先是透過靈糧堂趙世光牧師的口,將宣教的熱忱放入他的心裡,並且藉著宣道會資深宣教士包忠傑牧師(Paul Henry Bartel)說:「普世宣教如同世界運動會的接力賽,猶太人跑過了,歐洲人跑過了,美洲人也將跑完了,現在輪到東方人接棒了。」 鄭果也進一步從聖經中看到,主耶穌的大使命是向所有的基督徒頒布的。因此他關心同胞的心油然而生。他既有這心志,神就在他離港前透過佈道大會與個人探訪,帶領了600多人信主。
在播道神學院執教6年後,鄭果內心有感動要去牧會。在求問神的過程中,神藉著趙君影師母的講道,將南洋華人教會的需要帶給了他。趙師母特別提到菲律賓需要會講閩南語的牧者,這樣的呼召加上使徒行傳第八章的印證,使鄭果感到神的帶領是在南洋的菲律賓。在安靜等候中,他接到菲律賓馬尼拉靈惠堂的聘書,於是他認定這是神的帶領。因應需要,香港播道會執行委員會決定按立他為牧師。1959年5月10日在播道會天泉堂為他舉行了按牧典禮,他的按牧團包括鄭德音老師、鮑會園牧師等人。同年6月,鄭果帶著神對他差傳的負擔離開香港,搭乘輪船前往菲律賓。
三、在菲律賓
菲利賓靈惠堂源於靈惠中學(Grace Christian High School),這所學校是李錦英校長與宣教士白愛恩牧師等人於1950年所創立的,他們藉著辦學,推行基督教教育,拯救人的靈魂,並設立了地方性的教會。1958年,該教會改名為「菲律賓基督教靈惠堂」(Grace Gospel Church),次年聘請鄭果前來牧會。
鄭果的到來,受到靈惠中學和教會的熱烈歡迎。此後他開始了繁忙的牧會工作,每週忙於主日講道、晨禱會、探訪、查經會和禱告會等,生活過得極為充實。1959年冬,鄭果擔任了馬尼拉基督教青年會的佈道大會講員,在一連五個夜晚的聚會中,他傳講「主快再來」的主題,每場聚會都坐滿了人,許多人或蒙恩得救,或生命重得造就。
但到馬尼拉半年後,鄭果曾有辭職回香港的打算,原因有三:第一、是因馬尼拉四季如夏,炎熱的天氣,讓他吃不消,經常汗流浹背;更困難的是因為在室內有空調,到戶外曬太陽,這一冷一熱,常使他感冒。第二、他原是個教書人,教書人有「清高不求人」的個性。但成為牧師以後,就要以別人的益處為益處,這對他來說很不習慣。第三、他有個錯誤的想法,以為傳道人是領導教會的,在教會裡凡事都要接納牧師的提議。因為有人否決他的提案,讓他很受傷害,所以就產生了打道回「港」的念頭。但是神再次讓他看到自己的不足,要他對付自我,並以主為中心。經禱告之後,他才打消退堂的想法,從此專心留在馬尼拉。這一留就是16年,直到1975年6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後才離開。
初為傳道人,有許多需要學習的地方,從講道、帶查經,到探訪、送終、安慰,在沒有師母協助的情形下,他得事必躬親。蒙主的恩典,神首先將他的心改變。他開始關心會友的靈性、家庭的狀況、身體的健康、以及學業和事業的前景等。其次,他原先很膽小,害怕見到臨終的人。但神改變了他,使他能以愛來勝過,從此他對痛苦的人更有憐憫心。最後,是神給他禱告的恩賜,使他能為病人禱告,不少次神因著他的禱告,使癌症病人得醫治。在16年的事奉中,他學習不求從人來的尊重,不求從人來的榮耀,以母親般的慈愛,以恩慈待會友;以父親般的嚴愛去警戒不守真道的、勸勉軟弱的、安慰傷心的人。同時他自己也滿有生活的見證,勤勞多做主工,藉著他使主的名被尊重、被榮耀。
在靈惠堂牧會的頭兩年,鄭果注重「個人佈道」和「門徒訓練」,開辦「個人佈道講座」,訓練會友個人佈道的技巧。他強調從事個人佈道,心裡面要「熱」與「愛」。接著,他從個人佈道發展到家庭佈道,再擴大範圍到學校佈道、醫院佈道、下鄉佈道等。因著他在靈惠堂所推廣的佈道工作,使教會人數很快增長起來。
靈惠堂原是借用靈惠中學的課室聚會的,在1963年的一個主日,教會收到一筆70元菲幣,說明做為建堂之用。鄭果將此視為神的提醒,應該籌備建堂了。很快他們在山打米薩區的賓那街購置一塊地,然後開始建堂的信心奉獻。建造新堂所需大約等同十萬美金,皆由會友按照聖靈感動而奉獻。有人將部份養老的錢、有人將部份結婚的錢都拿出來奉獻,結果所得款項正好是建築所需的費用。1964年新堂始建,在建堂過程中,弟兄姐妹們日夜趕工,以至於許多同工被累倒。新堂終於在1965年9月竣工。在新堂奉獻典禮上,共有五百多人參加,臺灣的吳勇長老應邀證道。由於新堂仍不敷應用,於是他們在1968年再次購地,在正堂後面興建了「青年福音中心」。1972年,一座堂皇的建築落成於馬尼拉市。
鄭果早在50年代就對華人宣教有負擔。1961年,也就是他到馬尼拉牧會第三年,就開始發起教會的差傳事工。這事起因於駐菲大使館總領事李欲生長老,有次他由呂宋島中部回來,報告當地的描市需要華人宣教士,請靈惠堂過去幫助。同工們經過禱告認為這是神的呼召,那時教會詩班的陳惠美姊妹,剛好從菲律賓聖經學院完成學業,於是教會就差派她去描市,從而成為靈惠堂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當時靈惠堂每週聚會人數只有百餘人,經濟力量並不大,故教會內反對的聲音頗多,但鄭果認為任何理由都不可違背主所頒佈的大使命,於是他毅然差派了陳惠美前往菲律賓中部宣教。從那時起,靈惠堂每年都會差派一、二位宣教士出去。自1965年完成建堂後,他們更加快了差傳的腳步,組織成立了由鄭果負責的「靈惠差會」,並在教會內掛起一張大幅世界地圖,上面標明了宣教工場,也安放了宣教士的像片,使會眾瞭然於心,並為之代禱。在這幅地圖的上頭,寫了幾個大字:「菲律賓是我們的工場」,過了二、三年後,又改寫為「亞洲是我們的工場」,最後改寫為「全世界是我們的工場」,以此提醒教會要不停地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到1966年正式成立差會時,靈惠教會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已遍及菲律賓、日本、中國、印尼、泰國、汶萊、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亞洲八國。
為推動差傳,鄭果每年都舉行宣教年會教育會友,提出異象使會友認同,並鼓勵他們藉著禱告、金錢奉獻、與獻身差傳來參與。他們信心的奉獻逐年增加,從起初1966年的28,500元,到1972年的260,000元。那年教會一年的總預算有三分之二的經費是用在差傳上。在1973年靈惠堂派出在菲律賓以外的國家的宣教士有20位:日本4位,台灣4位,巴基斯坦1位,印尼3位,馬來西亞1位,北婆羅洲7位。到鄭果於1975年離開靈惠堂時,該教會差遣及資助的宣教士計50位以上;而教會用於差傳的經費佔教會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1974年7月,鄭果參加了瑞士洛桑福音會議,那次會議在洛桑大球場舉行,由美國著名佈道家葛培理講道,共有三萬人參加,會中有二千人決志信主。這次大會使鄭果深深感受到神的大能,也對他後來參與華人福音運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鄭果在菲律賓也參與了菲律賓聖經學院的籌備,這所學校的建立是為鼓勵菲律賓的華人基督徒願意奉獻自己的孩子,讓他們獻身並參與服事神。
鄭果在帶領靈惠堂期間,神要他學習如何謙卑地帶領長執會。首先,他看到人都不完美,但是長執會的同工以及他自己若能在主的話語光照下順服神,在個人屬靈的生命上有所追求,就能有更好的事奉,看中「人的生命」遠大過看重「所要做的工」。其次,他認識到牧者與教會同工的關係,既不是凡事以牧者的決定為最後決定;也不是由教會同工來主導,乃是牧者與長執互相尊重,合作商討,牧者肯容納長執的意見,長執能尊重牧師的指引,大家以愛相繫,就能和睦同居。所以追求合一就成為鄭果牧會時,非常看重的原則。如果教會為某件事工發生爭執,他寧可暫緩工作的進行,也要保持合一。此外,他也認識到「管好自己的口」是件很重要的事。傳道人常有一種失敗,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口,如果在牧會中遇到困難,或是不公的待遇,或是在長執會受到打擊,就會向合得來的肢體傾吐,結果人家有意或無意的傳出去,使他或別人受到傷害,這是很不智慧的事。鄭果學習到對傳道人來說,最好的傾聽者是主耶穌基督,如果心中有甚麼痛苦不平,就將心中的話告訴神,求神來帶領、解決。最後,就是要以聖經為依歸,只做符合聖經原則的事,例如合一、相愛、公義、聖潔、不論斷、不結黨等等,在基督的愛裡與同工們建立好關係。
在菲律賓牧會期間,鄭果也曾經有過胃痛出血的經歷。事發於去日本帶領聚會,因為飲食作息的變更,而造成了胃的損害,使他在東京的醫院住了兩週。回到馬尼拉後舊病復發,又去醫院住了兩週。這胃病前後拖了三年才得以完全康復。病痛中,他體會到生命的主權不在自己手裡,要抓緊機會為主工作;同時他也認識到傳道人自己應該看重身體健康,如此才能為主所用。病中他也深切感受到弟兄姐妹的愛,並學習在病中為會友禱告——在病床上按著會友名冊,一個一個的提名禱告。後來他一直保持著這個習慣,直到他離開世界。
到1975年,鄭果在菲律賓牧會已屆16年,他從40歲到56歲,教會的規模也從數十人發展到數百人,差傳的推動也已經快15年了。因著差傳工作,他常年在外,以致影響本堂的牧會,這時他意識到必須要在牧會與差傳之間做一抉擇了。經慎重禱告後,加上他看到各地華人教會對推動差傳之需要,使他清楚明白後者是神要他做的選擇。那時北美的教會紛紛邀請他去帶領差傳的推動,因此他於1975年5月離開菲律賓,來到美國,在東西兩岸奔波傳遞差傳的信息。當時他禱告,若是在美國有差會或機構要聘請他參加,那他就視為神對他的帶領。當他到了舊金山,去柏城(Petaluma)探訪中國信徒佈道會(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簡稱「中信」),會見總幹事王永信牧師與副手遊宏湘牧師時,他們當即就邀請鄭果加入「中信」,以開創差傳部門。因此他知道這事是出於神,於是就寫信給靈惠堂,向長執會解釋,為了普世的宣教,他必須離開主任牧師牧會的職務,並且請求接納自己成為他們的宣教士,為主做工。
參考文獻
- ↑ 宗教與文化.doc,豆丁網,2012-11-01
- ↑ 基督教的主要聖禮和節日,中國新聞網,2010-10-29